连环
张焕峥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自己岳母的葬礼上遇见大学时期的恋人。他猛地朝她站着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再也无法移动视线,直到她有朝这边望来的趋势,他才匆匆扫视过人群,抬眼去看岳母的遗像。他咬咬牙,努力忍着快夺眶而出的眼泪——就算忍不住,也得让泪水看上去是那么应景。
突然有人轻拍了张焕峥的肩膀,随之而来的客套话瞬间把他的情绪被堵了回去。“节哀顺变。”那人说道,听语气似乎是个十分善解人意的男人。
张焕峥缓缓转过头,发现身边站着个穿着得体的陌生人,他笑了笑,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“您是邓夫人的公子吧。”
“不,我是他女婿。”
“噢,节哀顺变呀。”
“噢”字的尾音让张焕峥尤其不爽,那是对他脸上的悲伤的嘲弄和质疑。不过归根结底,他的情绪虽然真挚,对死去的岳母来说也再虚伪不过了。男人马上对张焕峥失去兴趣,他和一些来参加葬礼的人一样,是来这里交际和攀权附势的,而他又明显从某个交际圈里听说了邓家女婿是个庸才这回事。他走开了,像条咬了一口硬骨头而失望的狗,但肉骨头遍地都是,他很快就能笑吟吟地摇着尾巴混进了某个正围着聊天的圈子里。
张焕峥的岳母是三天前病死的,死前的心愿是在老家办葬礼,但他丈夫在城里找了个好场子就赶忙把事办了,年近古稀的邓老恐怕是把老太太含糊不清的遗言听岔了吧,他以为只要把她葬在老家就好。
从早上开始,灵堂里就有高僧伴着哀乐在诵经,久而久之,张焕峥已经习惯了这些绵长又沉闷的声音,现在他又突然觉得聒噪,赶忙掏出烟和打火机,快步走出灵堂,准备去洗手间门口安静的抽会儿烟。刚抽完没几口,远处传来“笃笃笃”的急促的脚步声,抬眼一看,正是那个一直挂念着现在又最不想见到的人在朝这边走来。他木然地猛吸一口,只觉得嗓子呛得慌,他马上抬手紧捂着嘴,脸涨瞬间得通红,最后还是狼狈地咳嗽起来,看这阵势,似乎是想在厕所门口把堵在心肺里的疙瘩给吐干净。他试着伸手去扶墙,他想站直身子,想收紧正被压迫着的日益肥胖的肚子,想停止震颤,可刺耳的咳嗽声不断从口中传来,让他所做的努力给自己平添了一道滑稽。等他终于平静下来时,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,女人也已经站在他面前,他垂着眼睑,伸手用力擦着汗,好像在试着擦去刚才的尴尬。
“嗨。”她抬手冲他打了招呼。
话语还没脱口而出,张焕峥又咳嗽起来,女人笑着拍了拍他的背,匆忙地走进厕所。他瞥了一眼洗手台前镜子里的自己,发现也并没有那么狼狈,那弓着的身子、有些散乱的头发和始终夹在手中的烟,反而让他看上去显得更年轻了。他终于站直身子,把烟丢在地上踩灭并踢进洗手台下面的不见光的角落里,扯了扯领带走到镜子前,开始整理起头发。他有赶在女人出来前离开的念头,双脚却始终迈不开,他沉迷在了自己那被年纪给拉扯开的容颜上——至少提拔的鼻梁和漂亮的额头还和年轻时一样。
在清楚地听见冲水声前,张焕峥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两颊没刮干净的胡子上,他甚至试着去拔掉那些顽固又狡猾的黑刺,可惜那瞬间的疼痛只会增加如今的真实感,他开始为未来无限的可能感到兴奋,并为这种发自内心的兴奋感到焦虑和自责。他用清水让自己冷静,却在洗脸的间隙回忆起和十年未见的前女友的种种过往。不知从何时起,他就靠那些回忆和妻子生活着,他揣着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始终没有向生活屈服;他一直抱着会再见到她的侥幸,而在这侥幸之后,便是以为定能延续两人美好回忆的自信。现在看来,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
女人走了出来,他盯着她,眼神热烈,仿佛在盯着过去十年中的每一个她,他决定再也不让她离开自己的世界。
“嗨。”他后知后觉地打了招呼。
“你是在等我吗?”她问道。
“是啊,毕竟十年没见了。”
“你又开始抽烟了啊。”
张焕峥笑了笑,说道:“因为没有能让我下决心戒烟的人了啊。”
女人暧昧地笑了起来,岁月只在她脸上留下诱人的痕迹,她问道:“过得怎么样?看上去不错嘛,都胖了。”
“呵,我的生活——”他顿了顿,“我的生活像坨狗屎,我却愣是把自己养胖了。”
这猛然乍现的灵感简直就是张焕峥苟延残喘的灵魂发出的阵阵悲鸣,或者说,阵阵咳嗽。他马上为说出这样的话而沾沾自喜,毕竟,当初靠才华也吸引了不少女生。
“听说你娶了个好老婆。”
“好不好得我自己说了算吧。你呢,嫁了吗?”
“没呢。”
聊天中间突来的沉默在厕所门口也没有那么尴尬,它正是这儿的契机,女人先迈开步子,她没有朝灵堂的方向走去,而是面冲着走廊尽头的窗户。张焕峥紧跟在她后头,不断打量着她的背影,他开口打趣道:“再不嫁人就嫁不出去啦。”
“我还爱你呢。”
女人头也不回地说道,脚步不停,高跟鞋的声音像阵悲壮的号角,而对愣在原地的张焕峥来说,那是胜利的号角,那修长的背影便是触手可及的胜利。这一刻,他忘了妻子,忘了女儿,忘了一切道德伦理的准则,十年的煎熬让他自认为是个悲剧英雄,而英雄大概都有特权。
她已经走到了窗前,回头望着张焕峥,逆着光,突然就像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用最天真的口吻问道:“那你呢?”张焕峥无法从她的脸上读出这话到底是挑衅还是挑逗,他放慢脚步,变得小心翼翼,甚至有些不知所措,他假装没有听见,随口问道:“你怎么来这参加葬礼?”
“我认识邓先生,和邓太太。”她顿了顿,一句话中间的停顿有着无比深邃的空洞,仅凭咽唾沫的空当,她便能从那里平复情绪和提出勇气,她提高嗓音说:“——我问你,你还爱我么?”
如果再年轻十岁,张焕峥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拥抱她,再把心声一吐为快,可如今他却犹豫不决,像一只盯着人类手中食物的野鸽子,半张着翅膀,畏首畏尾。
灵堂里的哀乐戛然而止,张焕峥快要惊出一身冷汗,余音开始在耳边环绕,他不由自主地陷在了里面。他侧过身子,透过灵堂的侧门望进去,正好看见妻子邓欣然仰着脖子、左顾右盼的从里面走出来。她看见自己的丈夫,马上冲他喊道:“焕峥,快过来,准备出发了。”说完,她转身又走进灵堂。
“她是谁?”女人问道。
“她就是我妻子。”张焕峥边说边快步朝她走去。
“怎么觉得有点眼熟。”
话音刚落,他已经被紧迫的时间给推到她面前,一把将她揽在胸前。他埋头不断说着炽热的情话,他甚至来不及思考就脱口而出那大把大把让她听了浑身颤抖的话,而情绪却逐渐平稳下来。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她说着把他轻轻推开了,似乎带着摄人心魄的哭腔。
张焕峥不假思索的摇摇头,他在刚才终于下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,他婆娑着她的脸,说道:“我不在乎,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”
这时,灵堂里传来喧哗声,里面的人们准备散去,于是两人匆匆交换了联系方式,在没人看见的走廊角落里依依不舍的分别了。
葬礼还没结束,邓家人得把老太太的骨灰送回乡下老家去下葬。于是,老太太终于跟着邓家浩浩荡荡的车队踏上了归途。
天气晴朗,层层叠叠的白云如厚实的棉花垒在天际线上,马路有了尽头,气派的灵车掠过一阵又一阵翻滚的热浪,仿佛要冲进末端的云层中去。灵车后头跟着邓家儿子的车,再后头便是张焕峥一家子了。张焕峥坐在副驾驶上,上半身倚着车窗,左边肩膀冲着开车的妻子,好像在远离她;他抬眼看着因为车窗而变得有些暗淡的田野和山丘,有些漫长的车程将他藏在心中的愉悦消磨殆尽,又或者是因为情绪被藏得过于刻意而消失了,他得不断提醒自己才能拾起那份愉悦;可他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,上车后不久它就像冬日的夜幕一样不知不觉就披了上来,它的源头便是他用来美化懦弱的所谓的良心——他就是不能停止思考和分析一切自己出轨后即将面对的问题。
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制止自己胡思乱想,他在心里嘀咕着:“车上太闷了,要是谁能说句话——就算打个嗝放个屁也好。”
可车上只有他们一家三口,五岁的女儿躺在后座睡觉,刚失去母亲的邓欣然又显然不想开口说话。
眼前突然豁然开朗,原来是车子爬上了坡顶,湛蓝的天空扑面而来,午后的阳光猛地照进车里,张焕峥觉得自己被阳光呛了一口,鼻腔里充斥着奇怪的味道。后座的女儿惊醒了,她还没来得及揉眼睛,带着睡意、干涩的惊叹声已经脱口而出,车里终于有了生气。
张焕峥努力把身子探向后座,宽厚的腰背把座椅挤压地咯吱作响,他捏了一把女儿的脸,笑着说道:“漂亮吧。”
“嗯,漂亮!”
“刚才那女人是谁?”邓欣然冷不丁地*了句,张焕峥心里咯噔一下,以为她从刚开始就惦记着这事。他半张着嘴准备解释,她又像自言自语似得说道:“看上去有点眼熟。”
“啊,以前的同学,没想到她跟你妈妈认识。之前可能见过吧你们,是大学同学。”
“哦。”邓欣然毫不在意,“我们快到了吧。”
“这是你老家,怎么还问我呢?”他笑着说道。
过了有两分钟,邓欣然伸着脖子左右看了看,说道:“喏,前面那个就是了,村头变化不小呢。”
邓先生早就找人相中了一块墓地,是块能让邓家世代繁荣昌盛的风水宝地。今天那看风水的先生也来了,夹着个黑公文包,站在墓地旁恭候着邓家人。
快傍晚的时候,老太太的骨灰终于要下葬了,她的子孙们跪在墓前,看着她入土。张焕峥跪在最边上,一半的视野被帮忙下葬的乡亲不断晃动着的大腿给挡住了,他苦笑着,脑袋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埋在心里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场景。终于,他大哭起来。中年男人的哭声像灌进山林的风,呜呜作响,凄凉又渗人;他成功的压制了所有有气无力的哭丧声,积攒了十年的苦水终于恰到好处地喷薄而出;已经没人在意装着他岳母的那个精巧的盒子了,连他的妻子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风水师点点头说:“真是个孝顺的女婿啊,死者在天之灵一定能看到。”说罢,他手上抓了一把类似谷物的东西,往张焕峥身上撒去,张焕峥听见自己的身体被撞得砰砰作响。
半个月后,张焕峥还是再次见到了前女友,但他那日益肥胖的身子不断发出悲鸣,女人试着极力掩饰却又故意流露出的不满让他无地自容。终于,他再次走进了健身房。
他无疑是健身房里最胖、最会喘气、流汗最多的人,过于贴身的运动背心把他勒得像个正在增重的摔跤手,但这儿唯一一个秃头会员的出现让他心里平衡了多。
那是张焕峥开始健身的第三天,他在跑步机瞥见了一颗有些干瘪的秃头,等走过去一看才发现那竟是自己的岳父。在之前,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,但健身房里共同的归属感让他们瞬间都亲近了些,甚至忘了尴尬。张焕峥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生活的转机,他有时还会暗自感谢岳母的去世。
“爸,您怎么也来这健身了,吃的消吗?”张焕峥耸着鼻子,抓起毛巾夸张地擦起脸上的汗,好趁机遮住眼睛,让岳父有准备措辞的机会。
“诶,你看你妈生病走了,怪她身子骨不硬朗。我还想多活几年了,这不就来这锻炼身体了嘛。你又来减肥了啊。”
“您别说了。”张焕峥顿了顿,“我快被你女儿嫌弃死了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,又回到了各自的机器上。
几天后的傍晚,张焕峥从前女友处回家,在门口就听到妻子邓欣然在骂人。他开门进屋,女儿正在客厅自顾自地看电视。他走过去抱她起来,小声地问道:“邓佳佳小朋友,你妈妈在和谁吵架呢?”
“她在和外公打电话呢。”
“怎么吵起来了?”
“喏。”女孩指了指茶几,“妈妈看了一眼这个就打电话过去吵架了。”
只见上面放了张喜帖,张焕峥笑着打开一看,发现里面放着自己戴了假发的岳父和前女友的合照。老头咧嘴笑着,松垮的皮肤拧在一起,像一张抓皱了的纸;而那个女人——他已经看不清那个女人的样子了,只觉得她的脸和他见过的许多女人一样,长得漂亮又难以分辨。
他把喜帖扔到茶几上,啪的一声,那声音像他开除单位里某个公务员后,年轻人头也不回的关上他办公室的门时一样,绝望而又洒脱。他抬起手指放到鼻尖前闻了闻,上面还留着女人香水的味道,他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,所剩无几的中饭混着酸水快要从胃里涌上来。

 |我的勋章
|我的勋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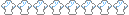
 :今日0 帖
:今日0 帖
 :风云0-1 届
:风云0-1 届
 Post By:2019-8-10 21:29:38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9-8-10 21:29:38 [只看该作者]
